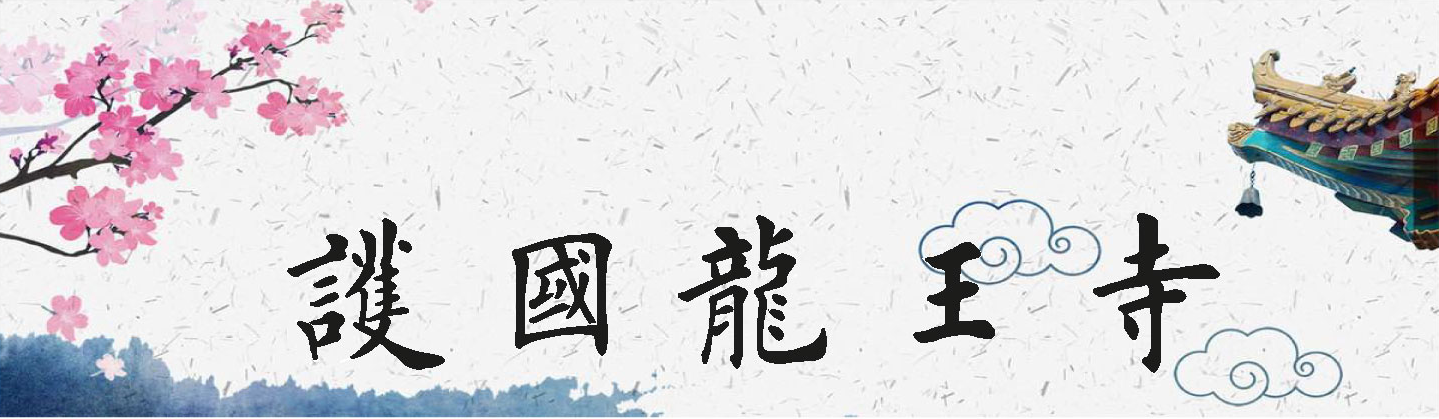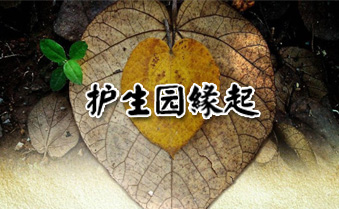大德法语 | French
放生: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宗教话题
上传时间:2015-01-04 10:37:37 点击次数: 次
放生: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宗教话题
一、放生现象:现代世俗生活中的异化生存
“放生”典出于大乘佛经,盛行于中国内地,西藏亦然,也流传于日本和邻近的韩国与越南等地。放生现象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所谓“吃它半斤,还它八两”;如果能够既戒杀又放生,当然功德倍增,此等感应灵验的事例史不绝书。放生的依据主要出自于两部经书,一部是《梵网菩萨戒经》,另一部是《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前者是放生的理论根据,后者是开设放生池的依据。其它大乘经如《六度集经》卷三,有赎□的放生记载,而另外玄奘三藏《大唐西域记》卷九,也讲到雁塔的故事(圣严法师,1988)。简言之,放生是从戒杀而衍生的,也可以说,戒杀的进一步必定是放生。戒杀仅是止恶,是消极的善行,放生救生才是积极的善行;如果仅仅止恶而不行善,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因此在中国,从北齐萧梁以来,便提倡断肉食、不杀生;且放生的风气也从此渐渐展开,从朝廷以至民间,由僧众而至俗人,都以素食为尚。而历代政府为了表示推行仁政,年有数日也定期禁屠;而从中央以至地方,或者为了祈雨禳灾,也都有放生禁屠之举。而放生现象整个深入基层民间的生活并和社会产生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则是在明末清初的时期才得以开展起来,当然这是与一些知名的佛教人物的大力宣传和推广分不开的;如明末莲池大师云栖祩宏就是历代高僧之中提倡放生最积极的一位,分别创作了《放生仪》及《戒杀放生文》使得大众在放生时对所用仪式有所依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放生行为作为一种流俗的社会风尚开始呈现商业化的倾向,其“为故而捉、放生即送死”、“放生先以伤生,戒杀还滋误杀”等矛盾当时即备受诟病。
改革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宗教政策日益宽松以及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类宗教活动在宗教场所和民间不断复苏,近年来则有更加活跃之势。在此背景下,放生行为这一传统宗教活动也日益恢复和增长,并重新成为当下流行的一种社会风俗。并且演变为一种社会流俗的放生行为在做法上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大型化、商业化、专业化的筹组企划,而非佛教中原先所指的随缘性的放生,这种建立于单一放生目标(即是所谓的积“功德”)上的行为也连带的促成了因大量放生而起的动物与物种需求;并进而引发了许多的商机存在,导致放生行为偏差为一种商业化行为(陈玉峰,1995)。最终的结果就是庙方、信徒、猎人三者形成一个企业化的组织架构,将动物商品化,并将放生行为操作化成一种标准化的程序,商业化的放生行为也成为放生文化在当下世俗生活中的一种异化生存状态。此类放生行为的重要特征在于非常注重放生行为的形式以及由此所积“功德”的质与量,而较忽视佛教放生教义不限时间、地点、场合,随时遇到随时起悲悯心而行放生,以“平等行慈故,普及一切”、“不起差别心”的忘相放生。具体说来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放生的物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乌龟成为放生者比较嗜好的选择,在放生者看来“龟乃四灵之一,放生乌龟的功效远大于放生鸟类”。因此,放生转变为目的论,是为求消业障、积功德,放生者大多相信放生的功德可以生命的条数计算,放得愈多,功德愈大;但却对放生行为所造的生物的死亡以及生态的失衡完全置之度外。二,放生者动机更多的倾向于消除业障碍,出现类似中古欧洲教廷之“赎罪券”倾向。因而放生信徒中有很多商人、建筑商、医生等,其放生行为往往基于某种良心不安或赎罪心态而事之。三,只在乎放生行为的抽象意义,而忽略生物实际生命之残害等系列问题。对放生过程中的捉、放、折损等问题,则以“动物之生死为其因果机缘,为我所不能控制”为理由自圆其说。
二、冲突或契合:放生行为结果的再审视
对于放生行为特别是商业化倾向的放生行为所导致的不当后果早在明代就为人们所认识,但是从那时起一直以来人们对这种不当后果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佛教教义的生命教育与追求宗教上的自我圆满途径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愈来愈多的由全球化所造成的议题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运动,其中由生态环保议题而生的环保运动成为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附产品在世界各地迅速开展起来。至此,放生这一过去习以为常、被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行善模式及其结果必须要拿到全球化背景下的环保运动语境中接受检视,而非仅仅停留在原来的宗教意义上。在环保运动语境中来检视放生行为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认为放生行为是与现代环保观念相冲突的,二是认为放生行为是与现代环保概念相契合的。
“冲突论”站在现代环保观念、动物权益的立场上,认为当下的仪式性、商业性放生行为会造成以下环保问题:一是造成野生动物大量死亡,加速野生动物的灭绝。在放生过程中由于受到浓烈功德论的驱使,放生者往往偏好放生野生、稀有动物以此来积大功德,从而诱使偷猎者捕杀野生动物。二是导致疾病或寄生虫的传播。三是外来物种可能会影响本地的生态系统。由于放生者往往不考虑放生动物的生存规律,可能会导致外来物种侵入放生地。外来种生物一旦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后,在缺乏天敌或人为控制情况,繁殖能力强的物种,短时间内种群即可快速膨胀,打破当地生态平衡。可能捕食当地原生物种,或是造成利用相同资源或栖地环境的竞争,因而排挤当地原生物种,导致原生物种族群减少甚至绝灭(颜仁德,2000)。
与“冲突论”相反,“契合论”则认为放生行为及作为其理论依据的“缘起论”、“护生观”等佛教教义是与现代环保观念相契合的,两者的契合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缘起论”当中的整体论思想与当代生态论理学的整体论思想相一致。佛教的“法身偈”曰:“若法因缘生,法也因缘灭,是生灭因缘,佛大沙门说”(《杂阿含经》卷二,《大正藏》第二卷),朴素地表现了佛教整体论的思想,认为整个世界是息息相关,因果相继,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而这是与现代生态伦理学所主张的“人类不过是生态系统整体中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平衡和谐的生态环境。”相一致。二是“护生观”中的珍爱自然、尊重生命的精神与当代环保观念中的自然权利学说相符合的。佛教的《金刚錍》曰:“我及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变、遍摄,世人不了大教之体,唯云无情不云有性,是故须云无情有性。”从根本上承认非人类生命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这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的“人之外的自然界都有与人平等的权利”相一致(郭冬梅,2005)。
比较两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冲突论”所关注的是放生行为特别是商业性放生行为造成的环保问题,“契合论”所关注的是放生行为所体现的佛教教义与现代环保意识间的相关性;可以说前者更多关注于行动的后果,后者则更多关注于行动的意义。事实上就护生的概念而言,要追求宗教上的自我圆满的提升可以通过许多生活实践的角度来进行,而不仅仅只凭放生这种仪式上的行为来获得自身的功德和慈悲行为的宣扬,那么为什么人们对放生情由独钟,放生这一传统宗教仪式商业化背后的推动力量又是什么?
三、放生行为的解释依据:理性选择、宗教资本与社会网络
如前所述,放生行为的理论根据来源于佛教教义体系,佛教的教义主要即是源起论与护生观这两种类别,而更以护生观为其最核心的道德规范精神之所在。佛教中所特意强调的生命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的因果律中所强调的一切果报皆来自于“业力”而促成,只有不断的透过行善的过程才能累计自我的福报以铺设良性的因果循环。因此这样的“因果循环”概念也就进一步说明了放生这类活动的要旨出发点不单单只是生命教育或修为心灵上的提升,同时也是一种背后带着浓厚的功德论的作用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功德论应该成为我们解释放生行为的最根本的立足点。
- 【上一篇】:北极熊雪中“相拥” 大秀兄妹情深
- 【下一篇】:理性选择